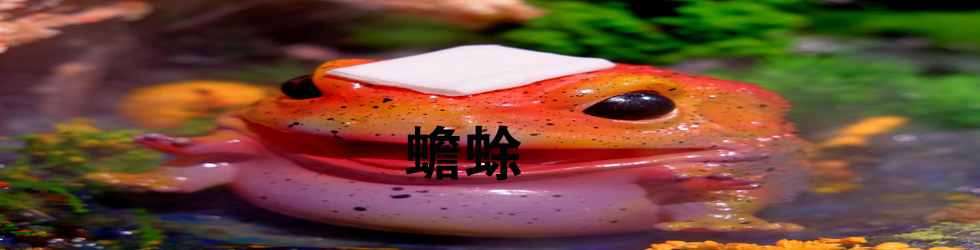没有月亮,镰刀一样的下弦月一定是躺在云层后面睡着了。天空黑乎乎的,天空的云层黑乎乎地没有了层次,天空下面的路和周围的事物也黑乎乎一片,模糊不清。
“都快点,磨蹭死了!”这是二哥的声音。从声音方位判断,二哥和姐姐已经走到草滩下和北具湾路的分界处——凉水泉。
像月牙一样的八把镰刀在二哥背篼里睡着,头顶着背篼的底,那是昨天傍晚父亲在月牙一样的磨刀石上打磨得铮亮的八把镰刀。父亲在昏黄的灯光下给二哥收拾背篼时,一定是把天上的那把镰刀不小心也一并儿装进二哥的背篼里了吧!要不现在还如此地黑。我在半醒半睡的状态里听见母亲反复叮嘱着二哥,走地里一定背好镰刀,其他弟兄都小,镰刀拿在手里摸黑走路不放心。姐姐不能背,姐姐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弟兄得照顾着点,何况要走远路。
“等卡,急死了!”这是三哥给二哥短粗而略带愤懑的回应,极速地穿过夜空,朝凉水泉二哥的方向射去。三哥明显心里不愿意,整天价上地劳作的三哥已经够累了,一季金黄的麦子变成了场里的大垛子,乌七八糟的麦茬地犁地平平整整黑黝黝的。还没轻松几天,秋田又要收割,又是一个一个早起晚睡的日子等着。此刻,我们四个小点的男子汉强睁着朦胧睡眼才刚走过樊家沟和北具湾路的分路口,还没真正走出庄。我们看不见路,三哥在前面拖着我们,我们像一串游走着的糖葫芦,手拉着手。三哥三年级毕业就不读书了,开始帮大人分担家务。他眼睛闭着都不会走错老家的沟沟畔畔,哪里有坑,哪里有水滩,一清二楚。
我在三哥后面,老六在我后面,四哥最后一个。老六还在梦中,高脚猛踏的凌乱脚步和拽不动的沉重身躯告诉我们老六的实况。四哥忽然喊了一声,“懒死了,还睡着呢,到地里了,赶紧起床”。
离今天要去的地里有四五里山路,我们充其量才刚刚出发。不过四哥的话倒是起了很大作用,老六挣开我的手去揉惺忪的双眼。我知道他醒过来了。
其实我们都在高脚猛踏地在黑暗里摸索着。二哥和姐姐在凉水泉原地等着我们,我们串成一串更大的糖葫芦,熟路的三哥领头,二哥近视眼还背着背篼,怕磕着碰着我们,当然是最后。再者,二哥后面还能时不时催着我们,老六太小,怕又睡着。
月亮怕是不醒来了,比老六还嗜睡,周遭还是黑乎乎一片。回头向村口看,住着几家子人的村口没有一丝亮气,还是黑乎乎一片,似乎也没有醒来。
红土坡传来猫头鹰的叫声,我有点紧张。有人说,猫头鹰叫会死人,我怕经过猫头鹰叫的地方遇见死人。翻过红土坡是马鞍山,马鞍山是村里常扔死娃娃了地方。我忽然毛骨悚然起来,从心底抖出一个寒颤,好在兄弟姐妹几个都在,否则我会止步不前的。
我家山后头的这块地总共五亩,南北向的长,东西向的宽。这是我家最靠得住的一片山地,从家庭联产责任制放到户以来,就从未落空过。有一年种五亩“咸农”麦大丰收,咸农麦杆子长麦穗大,一地收割了无数的手把垛。等麦子收割完,正好下雨几天,一地明晃晃的水眼,北具湾路也是一路水眼水泄而不通。眼望着架子车和牲口是派不上用场,我们弟兄六个只好踩着泥泞,一回一回往来背,整整背了五天。
三哥在西头用一根火柴的光亮看清了我们自家地的疆界,然后向东挪了一段距离又划了一根火柴分清了我家禾田(豌豆、青稞、冰豆杂和种植的一季作物)和胡麻的分界线。我们趁着火柴的光亮在地头一字儿排开,一个看不见一个,除了近旁弟兄的声息。天还是黑乎乎的,四周还是黑乎乎的,伸手不见五指,我们看不见禾田现在是什么样子,看来镰刀是用不上了。
我们开始蹲下身子用手扒。“先不要束挽,扒的禾田顺势放在身后,等天亮了再束”,二哥在黑暗里喊了一声。我们弟兄中,二哥从小说话算数,我们没有反驳他的习惯。“在自己的鞋底上或手上把泥根掸尽,摸着扒尽,两人之间不要落下禾田”,常务庄农的三哥补充了一句。
“沙沙,沙沙”禾田轻微的碰撞声,兄弟姐妹们向前挪动身躯时鞋底与土地轻微的摩擦声,似一曲曼妙的轻音乐开始在田间奏响。间或掸土的声音,像极了轻音乐里最响亮最要紧的几声鼓点。
泥土的芬芳徐徐飘过鼻翼,禾田的清香在空气中弥漫着。我能闻出里面还夹杂着小蒜花的味道,青草的味道,山丹花的味道。
“哎——”“吆——嚎——”二哥时不时直起腰板胡乱地大喊几声,击碎这夜曲中曼妙的音符。二哥说,听到声音,狼就不敢来了,把禾田里的虫蛇吵醒就走开了。我们信,三哥不信,他说你一个人的声音是故意招惹狼吧!于是我们都开始偶尔大喊几声,给自己壮壮胆,给看不见的来还是没来的我们此刻不知道的狼提个醒,警示它们我们的人多势众,惹不起。
青蛙和蟾蜍似乎是不怕我们早先給它们的警示的,我偶尔能感觉到我的手碰到禾田时也偶尔碰到它们的那种异样的感觉,它们直到这时才慢慢挪开它们鼓圆的身躯。我们叫“暴君”和蚂蚱的蝗虫也是不怕警示的,它们似乎把黑夜当成了正午,人不赶它不走,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子。它们在黑暗里向前跳一下,等我们扒禾田再接近,它们再往前跳一下,不离不弃。
一如地黑暗,时光像停在黑夜的某个点上,或者是夹在黑夜的某个缝隙里滞留着。但我们忙碌的手没有停下来。蹲着的身躯向前蠕动着,过了那个小沟沟子了,脚下有了起起伏伏的土疙瘩;现在过了那个凸起的塝塄子,死红土的禾田有点长势不好,有点短;那个下雨爱出水眼的地方也过去了,手边能感觉到灯花的大叶子了。
我们能感觉到那块三亩地的禾田已经扒了一半。四周还是黑乎乎的,但此刻如墨水瓶的天空,像是被一个淘气的小孩往里掺和了些许水一样,颜色清淡了点。我们彼此能看得见身影了。东边最远处白家沟石沟那里的天边有了较白的云彩在翻腾,那是最亮的地方了。
山后头梁豁线上远远传来母亲的咳声。“哎,操心着早起来烙馍,把时间看错了,长针看成短针,你们走了,我八个馍馍烙熟又看表,才一点半”,这是母亲把背着一背篼麦柴放下时说的话,是对自己的抱怨还是对我们的内疚,不得而知。看到我们收割过的如此大的地场,母亲还是不忘狠劲地表扬几句。
一堆火像一团红红的太阳升起在田地,我们站在火堆的周围,看着彼此满脸满身的泥土,我们相视而笑。我们的身影,像一条条被拉长的太阳光芒铺在地上,却没有光亮,光亮在我们的脸上。
“沙沙,沙沙”禾田轻微碰撞的声音,鞋底磨擦泥土的声音,掸土的声音再次在田间响起。这次的乐曲里,多了母亲不断的咳嗽声——最不协调却最美丽的音符。
当东方的云彩还撕扯着半轮红日的时候,我们的身影已经在山后头梁豁线上,跟随着母亲的咳嗽,朝着西面箩湾梁的另一块田地走去。
(甘肃天水宋月定年3月11日于尚德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