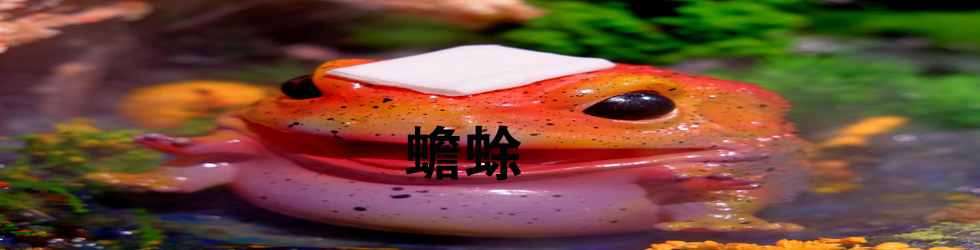文丨认知历史
编辑丨认知历史
前言汉代是中国神话形成的重要时期,以月亮为中心的神话体系也在此时逐渐形成。但目前学界对汉代月亮神话图像的研究相对较少,仅有几篇关于其图像艺术特征的论述,缺乏对其整体观念、社会功能以及审美特征等方面的研究。
因此,本文拟从多个角度对汉代月亮神话图像进行研究,以求深入探究其背后所蕴含的意义。
本文通过对汉代月亮神话图像的地域分布、神性人物、动、植物及形成动因等方面进行考察,以揭示汉代月亮神话图像背后所隐藏的主题和意义,并将其置于汉代社会思想、文化、政治等大背景下进行探讨,以期对汉代月亮神话图像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汉代月亮神话图像的地域分布通过对《汉书》《艺文志》《太平御览》《文献通考》等古籍文献的相关记载进行统计,我们可以发现汉代月亮神话图像主要分布在西王母信仰发达的地区,包括四川、重庆、湖北、湖南、陕西、甘肃等地。
首先是西王母信仰比较发达的地区,如四川地区的巴县、涪陵等地,以及重庆地区的巫山等地。这类地区普遍存在西王母信仰,且其建筑遗迹和墓葬中均有西王母图像。
此外,在这类地区还有一些较为特殊的建筑遗迹和墓葬,如湖南湘西的凤凰古城,四川彭山出土的“汉王母石棺”以及出土于四川成都武侯祠的“西王母像”等。
这些西王母图像及其墓葬群不仅集中分布于汉代西王母信仰发达的地区,且与汉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也基本一致。
其次是四川地区,如重庆地区的大足石刻群。这类遗址主要分布于四川盆地西北部,除大足石刻外,在整个四川境内还有不少发现。如成都市郊大邑县安仁镇出土了一尊“西王母”立像以及西王母墓。成都地区出土了不少与“西王母”相关的建筑遗迹,如“王母阁”等。
再次是湖北、湖南、陕西等地。湖北地区因其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地位等因素,在汉代月亮神话图像方面表现较多,如湖北襄阳市出土了一尊“西王母”立像和西王母祠。
湖南地区在汉代时曾一度是楚国的势力范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楚文化逐渐被湘楚文化取代,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在湖南地区出土了大量以“西王母”为主题的建筑遗迹和墓葬群。
如湖南湘西凤凰古城的“凤凰西王母”庙,湖南郴州永兴县的“西王母祠”以及湖南郴州市苏仙区的“西王母墓”等。
汉代月亮神话图像中的神性人物据现有资料可知,汉代月亮神话图像中有两位神性人物:一位是月亮本身,另一位是月亮的配偶“嫦娥”。
汉墓中出土的大量墓砖、画像石上都有关于月亮与嫦娥的图像,“嫦娥奔月”神话也已在民间流传了上千年。通过对这些图像的分析可知,月亮本身是一位女性神性人物,同时也是一位具有配偶“身份”的神性人物。
根据考古发现,我国最早出现“嫦娥奔月”神话图像的墓葬为东汉永平九年(公元68年)河南洛阳偃师白家洞汉墓,墓室南壁西壁和东壁北端分别绘有“嫦娥”和“吴刚”二人持桂枝、丹药之像。
两人手持桂枝、丹药,分别象征着嫦娥的月宫和吴刚的月宫。这两位神性人物或为夫妻关系,或为主仆关系,均具有“配偶”身份。
关于月亮配偶“嫦娥”,目前发现最早的记载是西汉初司马相如《上林赋》中有“众星之繁会兮,月亦与之俱行”的句子。
司马相如作为西汉著名辞赋家,其笔下的《上林赋》不仅是汉初文学作品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而且也是现存最早的一篇长篇赋文。在该赋中,司马相如用“众星之繁会兮,月亦与之俱行”的句子描写了月亮与其配偶“嫦娥”之间的关系。
《上林赋》是现存最早的一篇长篇赋文,其中对月亮与其配偶“嫦娥”之间的关系有如下描写:东方朔曰:“臣闻之:‘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
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明德不惟民之德。
汉代月亮神话图像中的动、植物在汉代的月亮神话图像中,植物也是一个重要的主题。植物主要指生活在水中或地上的植物,这些植物往往与月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在汉代的月神信仰中,还将植物纳入了神性人物的神格之中。
在汉代,“月神”信仰主要表现为对月神祭祀的重视和对月神人偶的崇拜。如《汉书·礼仪志》记载:“汉初以岁首冬至,设神主于太一,陈其事,旦为春官,暮为夏官,以待四时之祭。其祭具谓之天爵、地爵、人爵。”
而在汉代常见的月神祭祀活动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祭祀天地”和“祭月亮”两种。
在汉代,月是农业生产、生活和宗教信仰不可或缺的重要象征。在农业生产方面,汉代月神祭祀活动不仅具有“祈谷”的功能,同时也有“报时”和“报年”之用。
在生活方面,月神祭祀活动既有酬谢上天的职能,同时也有为民祈福、消灾免祸、保佑人畜平安等方面的作用;在宗教信仰方面,月神祭祀活动不仅能够满足人们对于精神上的需求,同时也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现实世界之外的神秘世界。
除了月神祭祀外,汉代月神在其他领域也有所体现。如在汉代墓葬中常见的羽人、羽车、羽马、羽旗等。如《后汉书·礼仪志》记载:“汉以后之封禅之类,皆以羽人、羽车为之”;《汉书·郊祀志》记载:“其祭天也则升木而祭日;祭地也则升木而祭月;祭人也则升木而祭日”。
此外,汉代墓葬中常见的羽人、羽马、羽车、羽旗等也都与月神有关。
在汉代的月神信仰中,动物作为月神的重要助手,其不仅充当了“护卫”的角色,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沟通”的作用。
如在《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凡祠祭皆用牛羊,不用羊豕。以牛马祭天地、山川及百神之祀,皆有牺牲,祭天则升木而祭月,祭地则升木而祭日,祭人则升木而祭月。”
此外,在汉代月神信仰中,还出现了很多“月宫”形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桂树”。《礼记·月令》记载:“季秋之月,夜明三十刻。天子乃采桂一枝”在汉代的神话中,桂树一般被认为是月亮女神嫦娥的化身,也有人认为桂树是嫦娥的化身或她的一个分身。
因此,在汉代月神信仰中,桂树往往是人们崇拜的对象。在汉代月神信仰中还出现了众多植物形象,这些植物形象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而且也代表了当时人们对生命、对自然和对宇宙的认识。
如《礼记·月令》中记载:“孟冬之月……日在中天……无有行步(行步:行走)。日入于地……无有行步。”在汉代人们看来,植物是上天和人间沟通的使者和桥梁,而月神也是通过植物来实现与人间的沟通和联系。
此外,汉代月神信仰中还出现了“日入于地”、“日入于月”等形象。
汉代月亮神话图像形成的动因汉代月亮神话图像的形成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受民间信仰和地方文化的影响;二是受到汉代统治者崇奉之神的影响。
就前者而言,汉代月亮神话图像是民间信仰和地方文化的产物,在它们的共同影响下,共同形成了一个以月亮为中心,包括蟾蜍、桂树、玉兔等多种神性人物和动物的神话体系。就后者而言,汉代统治者崇奉之神,尤其是月神,也是影响汉代月亮神话图像形成的重要因素。
在汉代社会,月神及其神话体系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信仰和崇拜对象。其中,月神及其神话体系在汉初出现,受汉代盛行的神仙方术影响较大。
汉初道书中对月亮形象的描写,也与月神有着一定联系。《淮南子》说:“月离于毕”、“月离于毕”等皆是月神形象。可见在当时的神仙方术中,月亮已成为重要的神物。
《汉书·东方朔传》云:“(东方朔)至大帝庙夜梦人请曰:‘东方朔本胡人也今为神巫,能致神灵。’
此外,月神及其神话体系在汉代还与道教信仰联系在一起。如《汉书·王褒传》曰:“方士言:‘黄帝、尧、舜时官为巫史,服事东夷,以月支德为号’”。
道教将月神作为五神之一,认为月与道相通,道家遂将其视作“天帝”。东汉后期,道教中的月神形象开始以蟾蜍为主。
如《抱朴子》中曾说:“月神,蟾蜍也。月,月支之精,为蟾蜍之魄。故曰月支者,月之精也。其形如兔,其白如雪,其音如鼓,食之无饥,服之无病。”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中的月神形象已发展得相当完备:“月神曰:‘汝得为月神,常得天人以奉事。可先至三泉(三泉指太阴星君)祠一祭’”。
此时的月神形象已由蟾蜍发展为玉兔:“又有言曰:‘月支者,月之精也……其形如兔而白首,安得不以象?’”
笔者观点汉代月亮神话图像的形成,是受民间信仰和地方文化的影响,同时受到汉代统治者崇奉之神的影响。可以说,汉代月亮神话图像是由民间信仰和地方文化共同作用而形成的。
在汉代,月亮及与其相关的诸多神性人物和动物都与统治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受到统治者的推崇。如月亮、桂树、玉兔等都成为统治者崇奉之神。
统治者将这些神性人物和动物当作重要的崇拜对象,并以此为依据对社会民众进行统治,最终形成了一个以月亮为中心,包括蟾蜍、桂树、玉兔等众多神性人物和动物在内的神话图像体系。
汉代月亮神话图像形成后,在社会中广泛传播,逐渐演变成为了一个完整的神话体系。
参考文献1、袁珂.山海经校注[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4、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5、郭沫若.中国史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