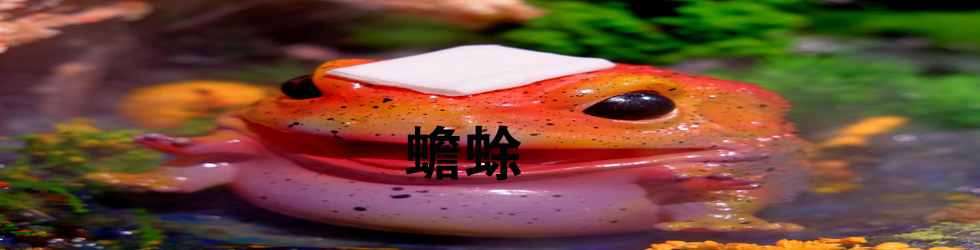“所恨的人离我们总是不远,有鉴于此,所爱的人,我们亦不能亲密到无间。”
这是电影开头的一句话,饱含人生哲理,却如此无奈和悲伤。预示着电影也欢快不到哪儿去,果然,灰暗的基调贯穿始终,连蓝色的大海都在低声呜咽。
不知道什么原因,主人公情愿到一个极其偏远的岛屿上工作、独处。迎接他的是一片戈壁般的荒凉,虽然不远处就是海,附近还有泉水解渴,但这是他心中的归宿。很快,他发现除那个胡子拉碴的老技术外,这个岛上还有其它类人生物存在,死亡的恐怖如影随形。
他找到灯塔中的技术员大胡子为伴,却发现其已经有了“亲密无间”的“女伴”,它竟是一名类人生物,被他们称为“蟾蜍脸”怪物。顺利进入灯塔与大胡子相依为命,每天过着吃饭睡觉打怪兽的日子,慢慢发现“女伴”是他的奴隶,整天打骂不算,还要时刻满足他的兽欲。日子过得很快,物资也马上耗光,面对怪兽他们逐渐陷入劣势。
生命将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末日狂欢的诱惑,主人公和大胡子的怪物女伴产生感情并在水中缠绵,成了地地道道的第三者。
可是,他们意外得到“水中空投”,用最古老难以相信不会漏水的潜水服潜入海底拿到空投。放几个“大炮仗”后,他们彻底扳回局势,但是屠杀残兵的时候主人公起了恻隐之心,并开始怀疑这样的屠戮是否正义。这个时候,我想到了晚清,西方帝国面对手拿大刀、长矛的长辫兵的时候,会不会也觉得他们是怪物,应该大杀特杀,把掠夺看成一种理所应当,当时他们有没有问过自己的行为是否正义呢?
主人公通过自己的调查、推测,得到一个结论——那些“怪物”之所以进攻,只是因为想救自己的同胞。他想和“怪物”谈判取得和平,却遭到大胡子的破坏,一气之下便去拼命。二人互戕后,大胡子被蟾蜍脸“怪物”吃掉,主人公拿起斧头,依然住在灯塔里,重复了开头的故事。
回头影片开头那句话——“所恨的人离我们总是不远”。
谁可恨呢?大胡子?还是主人公来岛前遇到的,让他产生厌世、孤独感的那些人?大胡子和那些人身边又有哪些可恨的人呢?
可恨的人,每个人身边都有,让我们改变模样的往往是他们,有样学样,逐渐变成自己最初讨厌的样子。主人公拿起大胡子那把杀戮的斧子,我们难道就“两手空空”吗?看看自己的手里、腰间,自省一下心灵、脑中,哪里不是插满斧钺刀叉?为了生存,生活所迫等等等等,每个人都有一百个理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却很少像主人公那样反思,试着做出改变。
个人如此,国家也是如此,所谓的帝国霸主有一个算一个,哪个不是四方用兵、欺负弱小,偶尔发发善心、捐点款、施舍点物资,梦想凭此树立博爱的名声。只有真正处于弱势地位的那些国家才知道,它们就是影片里的蟾蜍脸“怪物”,赤手空拳、任对方宰割,最好的结局就是成为“大胡子”的“奴隶”、“宠物”。
中国晚清时代不就是个例子吗?慈禧就是他们养的最大“宠物”和“奴隶”,和那个女怪物奴隶一般,“大胡子”说什么就做什么,不惜背叛国家,不惜毁灭种群。
“有鉴于此,所爱的人,我们亦不能亲密到无间。”
这是影片开头那句话的后半句,为什么不能和爱的人做到亲密无间?因为“可恨的人”总在身边,我们也在慢慢变成“可恨的人”。这句话用在爱人之间再合适不过,曾经的海誓山盟、你侬我侬为什么发展成后来的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因为互相变成“可恨的人”,没有了原来的“可爱和纯真”。
影片最后表现出一些细微的改变,大胡子走出灯塔时嘴里反复说了一个“爱”字,主人公没像大胡子出场时那样赤身裸体,那个怪物“女伴”也回到大海获得了自由。色调灰暗的影片里总算看到些希望,观影到此处,心情稍感放松和喜悦。可恨的大胡子死掉后,但愿主人公拿起斧头去砍柴,没有重蹈覆辙。
只是冒着黑烟的那些轮船让人很不爽,来岛的那些军官很不讨喜,看来身边总少不了那些“可恨的人”,主人公面临着又一次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