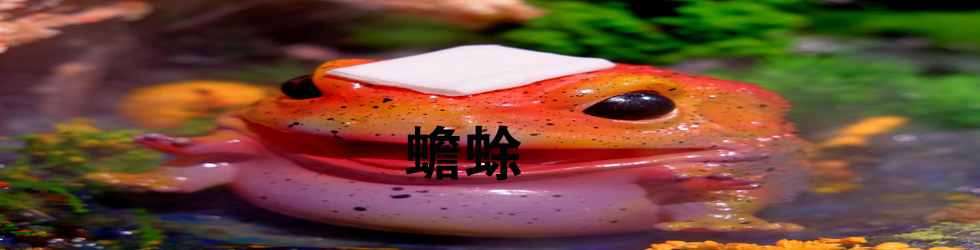《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芒种节到了,古代的村庄迎来农事繁忙的时候。不禁想起辛弃疾词里的村居景象:“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似乎各安其所,生机盎然,完全融入了村庄里的日常,然而实际上,诗人似乎只在一种情况下会注意到眼前的孩子,就是将人生抱负、世间烦恼暂时抛开,短暂放空的那个当口。
婴戏图是中国古代人物画的一个小类别,流传下来的画作不是太多。但其中反映出的童真,却是难得一见的。看着画中的孩子们行走在古松、奇石之中,你会觉得那些刻在审美基因里的苍劲风骨也在瞬间有了一点变化的趣味。
宋苏汉臣林间婴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我们也可以从诗人们的集子里找到那么几首和儿童有关的诗词,多半是在那些朦胧闲暇的人生片刻。比如杨万里《闲居初夏午睡起》:“松阴一架半弓苔,偶欲看书又懒开。戏掬清泉洒蕉叶,儿童误认雨声来。”诗人午睡醒来一派懒散,说想看书其实却连翻开书的热情也提不起来,只能做些更无意义的闲事,掬来泉水洒向庭院中的芭蕉叶。孩子听到水打芭蕉的声音,以为这是夏日午后的一阵雨。
画中也有这样的景致:夏天的庭院,白猫和花猫,曲院回廊,小石盆栽,绿叶缠绕衬托下的各色花朵,卧在凉席上的是一个穿着红色纱衣的幼小孩童。像是一张旧日的留真,为这个孩子的童年保存下来一份诗意。
宋佚名狸奴婴戏图波士顿美术馆藏图源:宋画数字博物馆
与童年相伴更多的是节庆的记忆。紧邻芒种的端午节,是夏日里活动最丰富的节日。画中红衣孩童手挑小木棍,拴住一只蟾蜍,正在逗弄蓝衣小儿,地上放着新鲜菖蒲和石榴花。画面右侧的蓝衣妇人在照看着较小的孩子,而左侧持扇而立的妇人则姿态娴雅,闲适旁观。
无款婴戏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蟾蜍是端午习俗中要趋避的五毒之一,民间认为毒性大的动物也能清热解毒,所以会在这时捉蟾蜍。小孩子在端午时以捉蟾蜍为戏,也是应此节景。菖蒲是端午节的“仙花”,有辟邪之用,而石榴花也在五月盛开,所以欧阳修写端午的词中有“五月榴花妖艳烘”“菖蒲酒美清尊共”等句,也说明这是两样必不可少的应节之物。
元人夏景戏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另一幅元代作品中,画面最前端的两个的孩子也在以蟾蜍作戏。后面两个抬着一张小茶几,茶几上放着钟馗像、瓶花、粽子和水果。蓝衣孩子手里拿着一柄宫扇,身旁露出侧脸的孩子拿着一枝石榴花。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个紫衣服的孩子,他正把一枝荷叶举过头顶。这幅“夏景”其实也是端午节的景象。
清人吴骞在《拜经楼诗话》里说,婴戏图、货郎图等画类之所以在宋代流行,是因为它们寄托了画家追思京城繁华旧事的回忆,所谓“不能忘情于故国故都者”。无论是汴梁还是临安,画中琳琅满目的日常,就是人们对承平时代的向往。
陈宗训蕉石婴戏图图片来源:宋画数字博物馆
“儿童未省承平事,只道丹青是梦华。”自顾玩耍的儿童自然体会不到这些成年人才有的思绪,于是他们就成为最无心机的代言人。将庭院中可以享受到的那一点点童年温馨慢慢扩散、放大,直至充满整个人生,然后在某一时刻,它会赫然击中你的心灵。毕竟在古代,儿童虽然不曾占据文学的焦点,但关于童心的种种说法却产生过很强的感召力。大思想家李贽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大书法家傅山从学童初写的不成字的书写中看出了天然奇古、颠倒疏密、不可思议,觉得其中有妙不可言的“纯气”。而大诗人龚自珍写了这首让很多人产生共鸣的诗:
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
既壮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
(龚自珍《己亥杂诗》)
栏目策划:三联·CREATIVE
责任编辑:牛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