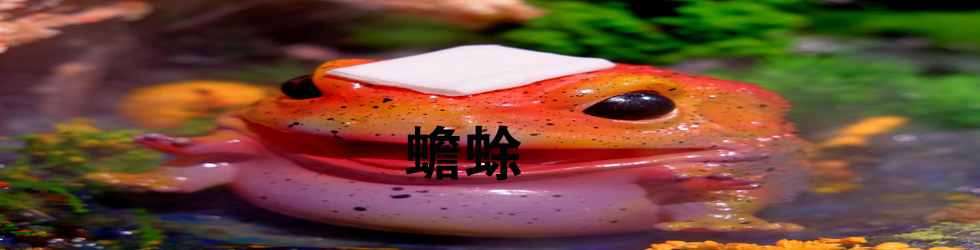当我们追溯陶瓷发展精神因素的源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陶瓷领域,精神因素的产生源于生存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双重作用。从生存方式的角度讲,陶器的产生源于定居生活,而定居的环境往往是大河流域的冲积地区,生产瓷器的原料较为丰富。
从生产方式的角度讲,人在形成之后,最早的社会形态是原始群,即人仍然保留着动物种群的社会形态特征。原始群进行着游猎和采集的生活,居无定所,其生存工具除简单的兽骨和经过加工的植物外,就是自然界中随处可见的石头,而石头经过人的加工,就成为了石器。
运用石器进行生存活动,在手法上属于雕琢行为。当然,这种雕琢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为了使石头更具有功能,使用的针对性更强。在使用石器的过程中,人们认识到一种特定的土壤具有可塑性,经火烧结后可以坚固成器,于是陶器便开始产生。
然而在这种土壤黏塑成形,并且可以形成器皿之前,原始人已经开始用它塑造人自身的形象,这种形象是人自身形象的写照,因而具有一种偶像的特征。然而这种偶像的精神意向并不清晰,而只有随着陶器的成型和发展,人类的社会形态进入母系氏族社会后,其精神意向才鲜明地显现出来。
原始群在游猎和采集的过程中,女性发现了农作物的种植技术,于是定居下来,使原始群产生分化。由于女性掌握着原始农业的技术和与之相伴的手工业制陶技术,因而社会形态朝着以女性为中心的氏族社会转变,而男性则或者从属于女性,或继续过着原始群的游猎生活。
而定居的生活体现出固定的文明的因素,因而留给今天鲜明的文明特征。这样,当人类围绕着女性进行生存活动的时候,也就使对于女性的崇拜得到展开,而崇拜恰恰是一种精神的追求。从陶器出现前那种模糊的泥塑人像,到完整的陶塑制品,反映出制陶技术的演进,以陶质材料塑造女性,反映出生产力的提高,上层建筑的重组和因此而形成的完整而鲜明的精神意向。
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陶塑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不仅继承了早期制品粗简、朴实的特色,而且扩大了表现范围。仰韶文化的陶塑,较多地成为装饰性制品,如甘肃秦安大地湾出土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陕西洛南出土的人头形器口红陶瓶,制作精巧,形象传神。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其口制成人头像。其像头顶左右及后部为长发,前额垂有整齐的短发;眼和鼻透雕成孔,鼻子较大,嘴则微微张开,两耳各有一穿孔。此制品将透雕、贴塑、刻画融为一体,具有以简示繁的独特功力,从而能引起观赏者的遐思。
人头形器口红陶瓶,器口亦制成人头像。其像塑造了一个女性,头部前额为短发,左右及后部亦为短发;眼和鼻透雕成孔,鼻宽,鼻翼鼓起,较上一件制品更明显地展示出人脸的本来面目。此制品利用迷着的眼睛,微启的小嘴,表现出此像是一个小女孩的头像,神情天真,充满稚气。
与仰韶文化为时大致相当的红山文化的陶塑则表现为另一种风格。辽宁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中,发现过一批小型的陶塑孕妇像。孕妇像头部残缺,上身前倾;右臂残缺,左臂横曲身前。手抚于乳房之间;肚腹圆鼓,臀部浑圆,生殖器刻画明显,足残。
在辽宁建平、凌源接壤地带的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中,发现的一件与真人头部大小相等的女神头像,头像五官较为清晰,目光炯炯逼人,嘴唇似在微启。此制品虽较残,但已生动地表现出形象自尊自信的精神风貌。很显然,这件制品反映的母系氏族社会中人们对女性和地母神的敬重与崇拜。
属新石器时代的制品还有多种。如龙山文化彩陶中,见有鸟头和陶祖塑像;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陶器中。见有见有陶壶上的堆塑裸女像。
陶塑女性形象的出现,是当时社会中女性占主导地位的真实写照。在现实生活中,就陶器本身而言,女性是陶器的制造者,也同时是陶器的使用者,因而人头形器口彩陶瓶上的女性和人头形器口红陶瓶上的女性,十分明显地反映了当时妇女的现实面貌,特别是与实用器皿相结合的工艺形式,反映出她们在当时的人类生存和日常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陶器这种当时最先进的生活工具的制作和使用上,她们是主要角色。
另如孕妇像、堆塑裸女像、地母神像则无疑是一种作为神来崇拜的女性。这种神像的塑造,反映出当时人类对于妇女作为社会的主宰者、人类生命繁衍的主要承担者所赋予的非人间所能具有的力量而对之尊崇和模拜的心理特征。在这里,人与神互相呼应,彼此渲染,以赋予人们无穷的精神力量。
有关妇女在新石器时代处于主导地位并被作为神来崇拜的历史,在其当时和后世被广泛传播,成为人们认识新石器时代历史发展的重要线索。这些线索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远古流传的神话传说,而这些神话传说则集中在女娲身上。除前面的例子外,还有很多,如“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女娲作笙簧”,“女娲祷祠,神祈而为女媒,因置婚姻”。
现代学者对远古神话和女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袁珂先生认为“古代神话产生于母权制时期,起初本是简单、零散的,后来才逐渐汇为比较复杂的整体,并且和历史紧密地结合起来。””有关女娲则认为“这个天神,神通非常广大,她毕生的功业,都表现在创造人类和补天两件事上”巴
再如何新先生对女娲的研究则更为深入:“女娲持矩,因其是阴神(地母),地方”,“因此,从文字和语音的角度考察,女娲就是月神女和亦即常仪(娥),她们都是同一名号的不同写法”,“原来,月亮神女娥以及华夏民族的母神女娲,其实都是从太阳神“羲”的名号中分化出来的”,“女螺与女娲(蜗)其实也是同一名号的异写”,“黄帝被表述成为月神与雷神交配而生的儿子……月神名女娲,螺祖别名雷祖,即雷神”。
从神女的角度来看,那件出土于红山文化女神庙中的与真人头大小相等的女神头像,塑造的应该是女娲的头像。从手段上讲,原始人类开始懂得用水掺和泥土可以塑成直观的,具体的形象,或者可以说是塑造人自己的形象。在这里,水土是自然界中十分普遍的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为重要的保证,所以从最直接的感受和需要来说,水
土是神圣的,是值得尊崇的。从精神上讲,用水土这样的生存保证来塑造人,当然不是简单地沉浸在人发现自己的形象可以再现的愉悦上,而显然是那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树立一个比一般的人境界更高的人可以显示自己内心的愿望,引导自己的行动,这显然与打制石器那种单纯的使用工具的便利考虑有所不同,于是,雕塑的意义也就真正地产生了。
但是原始雕塑不可避免地与打制石器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因为那时的神不是与人完全分开的,而是相互结合得十分紧密,因此由石器以及由泥塑人像共同启发的陶器,也就具有了精神和实用的两重意义。我们知道,在目前的考古发现中,作为器皿的陶器与作为陶塑的陶器都是最先出现的,后者的实例甚至更早,这就显示出精神与实用的鲜明特征。
在这里,神的塑造不是用于其他目的,在原始社会十分朴实的生存环境之下,是用于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直接地服务于人的日常生活,服务于人类生存。即使是那些神的色彩不那么鲜明的一般女性的写照,也不能脱离这一点。那些与器皿联结在一起的陶塑制品,既反映出女性与日常生活和制作陶器的密切关系,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对妇女的敬重心理。
对于女性的崇拜除以陶塑的形式展现以外,就是彩陶纹饰。彩陶纹饰中反映的女性以隐喻的形式表现出来。彩陶纹饰中的鱼纹、蛙纹、蛇纹都是间接反映女性形象的实例。鱼纹是女性生殖的象征,《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说:“有鱼偏枯,明曰鱼妇。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死即复苏。”
郭璞注曰“女姻,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同时,古代这种认识这已经得到许多当今学者的认同。如“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活跃因子,已经经历了上万年的变化发展,由图腾崇拜物到生殖信仰对象,都是早期鱼文化的重要功能。凡出土鱼纹彩陶的原始文化遗址就有二十多处。闻一多先生早就断言:由于鱼的繁殖力最强,而且与原始人类的崇拜生殖,重视种族繁衍直接相关”。
李泽厚说:“象仰韶期半坡彩陶屡见的多种鱼纹和含鱼人面,它们的巫术礼仪含义是否就在于对子孙‘瓜爬绵绵’长久不绝的祝福?”何新对蛙纹则有如下表述:“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娲或螺,在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中,乃是一种常被用作艺术表现的母题。
刘节《古史新证》曾指出‘赢’、三字,古书中常相混,而其本字当作‘嬴’,音与‘黾’通。在古代可用作浅水生物的共名,而更多的则是指蛙黾,也就是蟾蜍。了解了这一点,对于蟾蜍竟会成为月亮神女娲——螺母嫦娥的象征物,便不会感到奇怪了。但还应当指出的一点是,蟾蜍,以音近‘解鼍’(鳄鱼古名〉而与鳄鱼、蜥蜴共名。”
原始人类对于雕塑形式的接触要早于对纹绘形式的接触。特别是经过泥塑人像的塑造和陶器本身的塑造,人们可以轻松自如地以泥土的特性来适应生活,表达情感,而且随着这种制作技术的不断提高,使陶器更为方便于人类生活,使陶塑更为真切地模拟人像,使人们进一步加强了对塑的手段的信任。
而纹绘这种手段出现得相对较晚,其手法的运用还不很成熟,特别是真切地模拟人像,单独地表现他们心目中的神的形象,还不能满足当时人们的要求。如果说自然的生物可以隐喻人的世界,但自然的生物毕竟不是人,毕竟与人的生活有很大的区别,不能直接传达人的信仰和人的情感。而人的直观的形象不仅可以直接反映人的形象,而且可以通过表现手法的运用,如对称和夸张形式,通过特殊的对待,如放置于显耀的地方(神庙)。
又使塑像不同于现实生活中一般的人的形象,而是具有神的身份。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立体的,有一定厚度的形象要比平面的,二维的形象具有更大的分量,而陶塑形象的运用,正是要加大神的分量。在这里,空间意识已经服务于人们的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