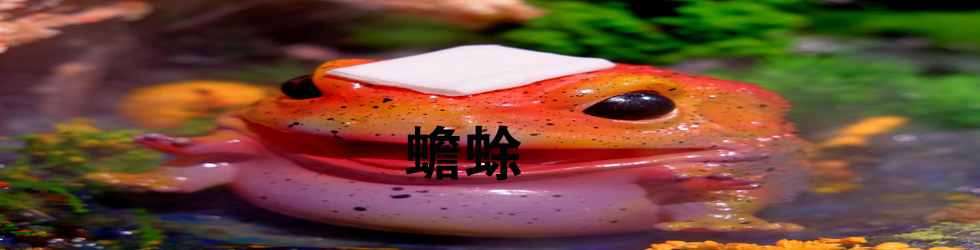中国传统节日中的习俗各地不同,但大体上都是遵循祖制,比如在端午节的时候插艾叶、赛龙舟,在中秋节吃月饼、赏月,元宵节猜灯谜,这些都是比较习以为常的。中国古代的端午节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其实远不止赛龙舟等活动,端午节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习俗——捕蛤蟆。五月五日官员、百姓齐上阵,这样的风俗在晋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之后一直延续到明朝末年。有趣的“捕蛤蟆习俗”自晋一直沿袭至明清,因端午节需要和人们思想的转变,古人研究出众多捕蛤蟆技巧,捕蛤蟆逐渐成为宫廷传统在晋葛洪的《抱朴子》里曾有过这样的记载:“肉芝者谓万岁蟾蛛,头上有角,领下有丹书八字再重。在这样的古书记载中可以看出,古人在五月五日日中的时候从蛤蟆身上取最需要的一部分,那么古人用蛤蟆有什么讲究呢?在明清时期,南海子位于北京南边郊区,这里是两朝的宫廷苑囿,每到端午节的时候宫廷里就会有专门的人去捕蛤蟆。随着人们思想的转变与端午节的需要,捕蛤蟆的技巧也越来越多。在《长安客话》里就说了宫廷捕蛤蟆的经过,太医院在每年端午节会被派来南海子捕蛤蟆,他们会挤出蛤蟆的“酥”来合成药材,制作紫金锭。当时一位姓张的管事,每次来的时候都会敲锣打鼓、声势浩大,那时候的人作了一首诗来嘲讽:“抖擞威风出凤城,喧喧鼓吹拥霓族。穿林披莽如唬虎,捉得蛤蟆刻眼睛。”把蛤蟆额头处流出的白汁用药自古有之,一般取汁的方法都是将蛤蟆眉间用针刺两下,这样蛤蟆大多就死掉了,这样就会减少蛤蟆数量,甚至用药也大不如前。所以这也是个需要技巧的活,一般人无法胜任。在一处乡野有位叫朱公儒的院使,他就拥有刺两针蛤蟆却不会死的绝活,一时间名声显赫。民俗学家张次溪也非常赞许朱院使的做法,虽然说蛤蟆是比较常见的,但也和人一样只有一次生命,如果只是取它东西作为药用却最后导致蛤蟆死亡,还是会于心不忍。除了朱院使的故事,民间还流传了不少关于捕蛤蟆的趣事。在《帝京景物略》里也曾记载,到了五月五日的时候,太医院的院官前来捕蛤蟆,他们到羊房南边的大柳树下坐着吃午饭。“顾旁一骷髅,来濡肉蒜盘,内骷髅口,戏问:辣否?骷髅曰:辣。来惊,去肉,辣音不已。遇到这样的事情大家都非常惊讶,所以下次再来捕蛤医院官员一起来的,而捕蛤蟆习俗也逐渐成为宫廷传统。因蛤蟆取汁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引发“蟾蜍热”,继而由蛤蟆衍生出的“紫金锭”作为赏赐物分发给大臣,成为维护皇权的手段,受政治牵制《本草纲目》是古代有名的医药书籍,中医药是我们国家独有的、令人骄傲的医学成就,在《本草纲目》中并没有记载捕蛤蟆,而是说蟾蜍。比如在这一句中描述取蟾酥:“或以手捏眉棱,取白汁于油纸上及桑叶上,插背阴处,一宿即自干白,安置竹筒内盛之,真者轻浮,入口味甜也。”这里的蟾酥应该是从蟾蜍身上取得,所以归属在“蟾蜍”名下,李时珍把蟾蜍和蛤蟆分门别类,十分严谨。在蛤蟆的记载中并没有用药的情况,他认为古法中的取蛤蟆用药和现在取蟾蜍用药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古人把蟾蜍称作蛤蟆罢了。所以说,史料记载的端午节“捕蛤蟆”实际上是“捕蟾蜍”的俗称,便于百姓理解和沿用。明宫廷中对于捕蛤蟆的记载最终也是归于蟾蜍一列,捉的是可以取出蟾酥的蟾蜍。上文中提到“紫金锭”在明朝人的医术中是叫“神仙追毒丸”,又有人说它是“太乙丹”。据说蟾蜍在五月五日这天鼓气最足,药效自然也是最好的,这时候就会有人来取蟾酥,它作为药引主要是协助制作紫金锭,紫金锭主要是治疗小儿症状,遇到中毒的情况只需要沾一下就可以立马止痛,非常有效。药效得到认可那么在经济领域就会引发一场蟾蜍热,百姓将捕捉到的蟾蜍卖出,再买进由蟾蜍制作出来的药品使用,自然形成一条以蟾蜍为主线的商业链条。对当时明清的经济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捕蟾蜍不仅对医学方面有很大帮助,这也是当时政治大环境背景下人们追逐名利的缩影。紫金锭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发给有功劳的大臣,这是明清皇帝政治统治的需要。同时,只有在较为宽松的背景下才能做到民俗的广泛传播。虽然后来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禁止了捕蟾蜍这类事情,但并不影响其制作品在官员面前的地位。张次溪对这样的说法也有过评议,他说宫里有很多东西都被传到民间,这样的做法也可以帮助民众解决问题,确实是能够证实的。”在宫里紫金锭是比较贵重的物品,本身就有保平安的意思,引得很多王公贵胄喜爱,而清朝的世宗皇帝也喜欢把紫金锭赏给那些得力的大臣,所以后来大臣们以自己得到紫金锭为荣。文化方面,端午节插艾草也是为了驱邪治病,古代重要的节日都是有着美好和谐的寓意,民俗活动从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中形成,逐渐有了清晰的脉络和道理,到了现代人们不会深究其中的奥义,但是祖上传下的活动一般也会传承下去。中华文明五千年,就是这样一脉相承,成为经久不衰的独特的中华文化。捕蟾蜍在现代很少看见了,但是中国农村还是会有蟾蜍用药的情况,早些年间孩子有毒物侵入的情况老人们也会取蟾蜍白沫涂抹,药效如何不得而知,但从这些小事中也不难看出传承下来的医药文化。蟾酥的具体功效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是“不详“,后人在研究时也没有确定其具体用途,但从古人对蟾酥的喜爱中也不难看到其对古代医药学的影响。单是以蟾酥作为药引制作的紫金锭就那么火爆,更不用说蟾酥本身了。清军入关后“捕蛤蟆”成为地地道道的民俗,不再受朝廷的干预,正式剥离政治外衣成为中国古代传统的民俗在生态方面,南海子这个地方捕蟾蜍的风俗一直都有,长时间捕捉必然会造成不好的影响,果然,在万历年间就有过这样的记载,礼部说医院都会派很多人去捕捉蟾蜍,这样会导致其伤残的多。用现在的话就是会导致生态不平衡,破坏了当地动物的食物链,这必然导致一些受蟾蜍制约的动物肆掠,加上这本来就是可以消毒的方子,平时宫廷里使用都不是很多,一些平民也来采取不免会影响到宫廷用度,所以应该严令禁止。礼部这样的建议虽然是向着朝廷的,但也确实为蟾蜍生存做出贡献,捕蛤蟆的人少了生态也得以维持。这个建议的必要性当时朝廷是非常清楚的,因为每年捕蛤蟆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参与,还有中官需要采办,捕捉的数量一旦多了,就会影响到当地海户和一些对庄家有害的虫类,既劳民伤财还会妨碍当地农事。不过虽然有这样的建议出来,也不能一下子结束捕蟾蜍的风俗,一直到崇祯年间还是有史料记载捕蛤蟆的场景:“北风五月骇扬沙,军令清街禁不哗。一道红灯驰郭外,中涓夜出捕蛤蟆。”所以说,万历时期礼部说的禁止捕蛤蟆,并没有影响到什么,久而久之就成为明宫廷一直沿袭的传统,不过后来到了清军入关的时候,南海子成为清朝的皇家苑囿,但是再也没有出现派遣当差的人去捕蛤蟆的情况了。从那以后捕蛤蟆成为地地道道的民俗,不再由朝廷的干预。其实端午节的一切民俗活动都和避邪驱病脱不了关系,蟾蜍被称为“月精“,月宫里传说有不死的药,蟾蜍一来可以辟邪,二来确实有药用的效果,就这样慢慢演变成一个习俗流传下来。在古人的医药中主要是取百草制药,神话故事中也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蟾蜍一类的动物大多生活在杂草丛生的地带,于是百草合药慢慢就到了蟾蜍用药。洁净去秽是蟾蜍的代名词,来自“月宫“的它更是会让人对它奇药的这个名号信以为真,民间的俗谚俗信是不会因为朝廷的禁止而销声匿迹,这也是一种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参考文献:《抱朴子内篇》《帝京景物略》《本草纲目》